
采访、撰文|杜鹃
十点人物志原创
生命旅程中,死亡是个无法逃避的话题。
而至亲的去世,也是每个成年人必须面对的人生课题。活着的人该如何消解“他已离去”的事实,始终是一种极其私人又十分复杂的情绪。
陪伴亲人走向死亡的过程,生者往往会充满遗憾、亏欠甚至悔恨。那些沉默无语的告别,看似悄无声息,直到再见与亲人相关的一切,情绪会彻底决堤。
65岁的徐舒,曾目睹癌重的母亲在生命末期孤独痛苦的离世,没有与母亲好好告别成了她心中一直缠绕的心结,令她深陷自责与愧疚。
半年后,徐舒罹患乳腺癌。她一面觉得解脱,欣慰于自己可以追随母亲的脚步,不用沉浸在对母亲的歉疚中生活。另一面深陷惶恐,母亲去世时的惨状,也让她对死亡恐惧万分。

母亲患癌后,徐舒带父母去海边散心/受访者供图
是否人就一定要在孤独和无助中等待死亡的降临?到底有没有不痛苦的死亡?徐舒发出深深地质疑。
为了寻求体面死亡的方式,她在机缘巧合下走进了海淀医院安宁疗护中心(以下简称海医安宁),成为一名志愿者。
随着近些年对死亡质量的不断讨论,临终关怀和安宁疗护事业慢慢走近人们的视野,其主要是通过安宁和缓医疗和辅助手段,帮助患者减轻临终时的痛苦症状和对死亡的恐惧。海医安宁便是全国首批示范基地。
成为志愿者的4年里,徐舒通过学习安宁和缓医疗和芳香呵护疗法,帮助临终的患者在爱与温暖的包裹下,实现生死两相安的升华。其中一位患者,是她自己的父亲。
这不单是一个关于死亡的故事,也关乎治愈与救赎。
在安宁病房与死亡擦肩的过程中,徐舒收获了一个全新的自己,她终于能卸下对母亲的负罪感,变成一个温暖、愿意对他人施以关怀的人,并更加从容地为自己的死亡做好准备。
没有对死亡的恐惧,人才能无忧地活着。
以下根据徐舒所著书籍《重启生命》与她的讲述整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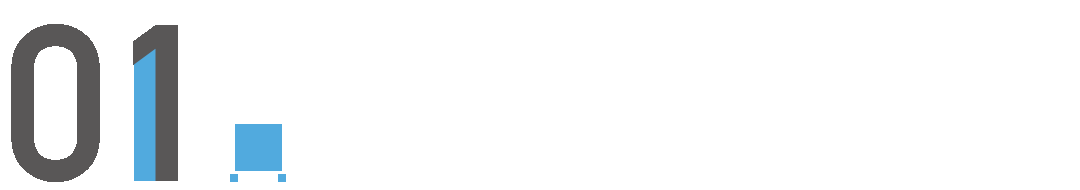
一堂缺席的生死课
关于死亡,有一个场景深深刻在我年少时的记忆中。
那人是姥姥的邻居,年纪比较大的一位老太太。在她生命的最后,儿子儿媳妇将她抬到了楼下的院子里,放在长凳上,身上还压了块烧柴用的木头。
老太太肯定是非常不舒服的状态,她口中有一口痰,每次一呼气嗓子仿佛破了一个洞,发出簌簌的声音,再一吸气,痰又糊住了嗓子。
当时我还小,不懂什么叫害怕,只觉得老太太很难受,就随处找了个小木棍想帮她把口中的痰挑出来。怎料,刚靠近她,就被邻家大人拎着脖领子拽到一边。
我看到老太太斜着眼睛望着我,仿佛能让她舒服一点的最后希望也破灭了,慢慢地,人就咽了气。
这次幼年时的经历,是我对死亡最初的印象。渐渐失去生活气息的老者、亲人们的哀恸,整个过程都算不上体面。老太太进入弥留之际时,家人都要把她搬出来,不愿她在家中离世,可见大家对于死亡的忌讳。
中国人对死亡习惯避而不谈,童年时死亡教育的缺失,导致我对死亡的理解都是社会和家庭侧面灌输给我的,死亡是黑暗、恐惧、痛苦、血腥以及晦气。
只是那时的我没想到,年少时所见的死亡,全然抵不过面对至亲离开时的震撼与痛苦。母亲的离世,是我刻骨铭心的噩梦。

徐舒的母亲/受访者供图
2016年,母亲肺癌晚期,癌症给母亲带来了很多身体上的症状,比如吞咽困难,脚趾头坏死,这些我都无法处理。跟大部分人的认知一样,我认为这时把母亲送到医院救治,才是孝顺,才算尽到儿女的责任。
于是,跟母亲商量后,在一个我终身难忘的礼拜天,我将母亲送到了医院。
进医院后,母亲的检查结果显示各项指标都不好,便被推进了呼吸科的ICU。ICU每天只有半小时的探视时间,剩下的23个半小时,都是母亲独自面对陌生的环境,听着仪器的声音。我虽然很心疼母亲如此孤独,但那时我依旧认为医院会给到最好的救治。
可当我第二天一早到了医院,见到的却是眼歪口斜,双手被绑在床上的母亲,像是中风症状,医生也递来了病危通知书。我很诧异,才一晚上怎么就病危了呢?
我询问护士到底发生了什么,护士说母亲昨夜疼痛难忍,双手不断挣扎挥舞,这么做是怕她误把输液管扯下来,早上已经上了止痛泵。
原本母亲身上贴着止痛的透皮贴,按理说不会痛到这种程度。而等我将母亲的单子掀开一看,两片透皮贴像被人掀开过,虚浮在母亲已枯瘦的皮肤上。

徐舒拍下母亲临终前的手/受访者供图
我当下一愣,护士解释说,她当时不知道这是什么就撕下来看看,又贴了回去。我惊呆了,完全无法想象母亲经历了怎样的痛苦,难道她就是这样在剧痛下硬挺了一个晚上,疼到中风吗?
气极的我想找值班的护士理论,此时母亲却望向我,口齿不清地说:“不疼了。”还用力挤出了一个笑容,我明白,她不愿我跟人起争执。
因为母亲有消化道出血的情况,医生停了营养液,也禁止母亲吃任何东西,我跑出去买了一杯甜豆浆,刚喂了3勺,喇叭就响起“不可以喂食”的警告声。
入院后我曾跟医生说,不希望母亲做有创治疗。所以当医生说要下个针方便输液,我也以为只是正常输液而已。可再次见到母亲时,她的右胸被开了个硬币大的洞,好几根管子直入身体。
更不要提,ICU里的空调冷风直吹在母亲身上,她本就怕冷,医院里也只让穿薄薄的病号服,身上只简单盖了一层白单子,我每一次去摸她的身体,都是浸入骨髓的冰凉。我曾跟护士沟通能否给空调加个遮挡,均无果。
进入ICU 5天后,母亲永远离开了我。本是想让母亲在医院得到更好的救治,却未曾想,只能眼看着她的生命在孤独无助中快速消逝。
在医院,病逝的患者要尽快从病房送往太平间,我推着母亲的遗体进入楼道角落的电梯,迎面扑来的却是一股腐臭,运送的人说,这是垃圾专用电梯。我心头一紧,原来人死后,要被当作无用的垃圾。

母亲病重时用的医疗设备/受访者供图
悲伤、无助如海啸般将我席卷,我不停地质问自己为什么要将母亲送来医院,就好像我在她最艰难、最需要温暖的时刻把她一个人丢到医院自生自灭一样。
甚至在我给母亲的遗体穿衣时,她胸口的洞还在不断向外涌出药液,浸湿了衣服也流了一地。母亲原本是极爱干净的人,却走得如此潦草,这个场面让我始终无法释怀。
母亲去世后的许久,我始终无法从自责的情绪中缓过神来。
那是面对至亲离世,却只能眼见她经历非人痛苦的绝望与悔恨,以及对死亡深深的恐惧。我曾想,到我死的时候,是否也要经历如此痛苦无助的死亡过程呢?
半年后,我确诊了乳腺癌,不知为何,我感到了解脱。我终于可以不用再充满负罪感,可以去天堂找母亲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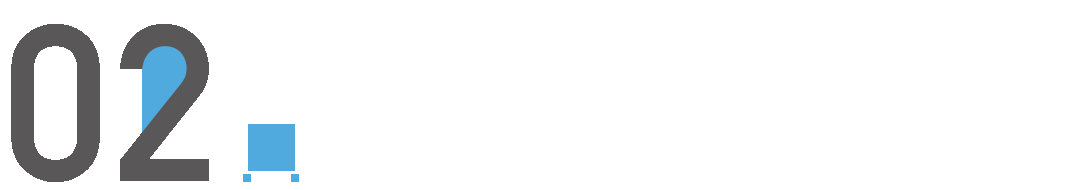
安宁呵护下,父亲平静的离世
但人生并不总是顺应人意,还在世的父亲成了我的牵挂,母亲去世也给他造成很大打击,每天神情恍惚。
有时父亲以为母亲还在世,夜里摸到我房间,坐在我身旁,说着该跟母亲说的话,在发现我不是母亲时,老泪纵横。
我曾在母亲在世时向她承诺,会照顾好父亲。为了遵守承诺,我积极配合手术,度过了放疗期,控制住了病情。
同时,为了不像母亲那样痛苦的离世,也为父亲的临终作准备,我开始寻找一种不那么痛苦死亡的可能。

徐舒的父母/受访者供图
我是幸运的,母亲的邻居是海淀医院血液肿瘤科医生秦苑,她曾在母亲被食物过敏困扰时给予过一些帮助,我便加了她的微信。
2017年7月份时,秦主任发朋友圈宣布海医成立了安宁病房,也是从秦主任的介绍中我了解到了“安宁疗护”的概念:帮助病情不可逆的生命末期患者,缓解身体的不适症状,可以有尊严、有温暖陪伴地告别这个世界。
我很感慨,遗憾母亲没赶上,又想着自己是否能通过安宁缓和治疗,平静地离开这个世界。
2019年,秦主任又发了条朋友圈,提及病房招募志愿者。为了抓住这个接近安宁病房的机会,我报了名,第一次特意背了个照相机,以能帮忙拍摄为由加入了志愿者团队。

徐舒在海医安宁志愿者活动中帮忙拍摄/受访者供图
7月6号,是我第一次进病房。我惊讶于这里的病房整洁而温暖,窗台上摆着小花盆,阳光倾泻而下,患者坐在床上和志愿者聊天,有种说不出的温馨感。
志愿者进门后,患者都会非常开心地与他们打招呼。志愿者们会依次帮患者洗头,对于无法坐立的患者,也会俯下身与他们说话。

徐舒在病房练习做芳香呵护
在海医安宁会用马甲颜色区分不同职责的志愿者。
红色是个案老师,一般是心理师和社工师,他们会倾听患者和患者家属的情绪,并分析情绪背后的真实诉求,从而帮助他们达成有效的沟通、四道人生,促成生死两相安。
绿马甲是普通基础服务团队,包括进病房给患者洗头,陪患者打牌,有时还会唱唱歌。其中理发师特别受欢迎,很多患者会排号理发,希望在生命最后也能拥有干净的仪容。
黄马甲是芳香呵护团队,志愿者使用精油或者不用精油,用手与患者进行肌肤接触,让患者在被呵护和关爱的感受中放松身心,使患者的情绪从焦躁不安逐渐变得平静,随着引导语放松身心后,有人甚至还能小睡一会儿。
经历了近半年的培训,我逐渐认同了安宁理念,也学会了芳香呵护,父亲便是在我的呵护下安详离世的,这也是让我十分骄傲的一件事。
2020年,我乳腺癌手术后以及放疗期间,无暇照顾父亲,跟父亲商量后送他去了养老院。
而后一年里,父亲经历了三次肺炎。一般老人生病,养老院的解决办法是通知家属将人送医。我实在不愿母亲的悲剧在父亲身上重演,在父亲第二次吸入性肺炎时,便跟养老院说我接受过安宁缓和培训,希望能在养老院照顾父亲。
我相信用安宁理念、芳香精油抚触等临终关怀技术,会比去医院效果好,最重要的是陪伴会给予亲人安全感。

父亲的背影/受访者供图
此时父亲仍是高烧不退的状态,出现谵妄,我也做好了父亲这次挺不过去的心理准备。我在线上紧急求助了一些志愿者伙伴们,请大家帮我提供一个应急临终呵护配方。收到了各个伙伴闪送来的精油,我们相约晚8点远程共同为父亲祈福。
8点整,在养老院父亲的房间里,我和哥哥便一人抚摸着父亲一只胳膊,开始为父亲做芳香呵护抚触。我在他耳边重复着引导语,让老人家可以放松自己,父亲捏了捏我的手,表示知道了。慢慢地,父亲放松下来,23分钟的引导语还没结束,他已经安稳地睡着了。
父亲离世时,表现也很惬意。离世前的一两天,他的眼神有时会从空洞变为清澈,也会对我慈祥的微笑。我心中隐隐感觉这是父亲在与我道别。我在他耳边告诉他,我陪在您身边呢,您是安全的,如果感觉疲惫,可以把眼睛闭起来,若是看到特别耀眼的光芒,也可以朝这那个方向走,那里温暖、有无条件的爱。
以前我做了饭菜,父亲如果觉得好吃,总会仔细品尝,然后满意地点点头。那天父亲也是这样,缓慢地咀嚼着,点点头,慢慢地咽了气。
在儿女的陪伴下,父亲走的很安详。我内心全然没有悲伤,没有遗憾,甚至还小有成就感。父亲这样离世是幸福的,用所学的安宁理念和芳香呵护帮父亲实现了善终,我也是幸福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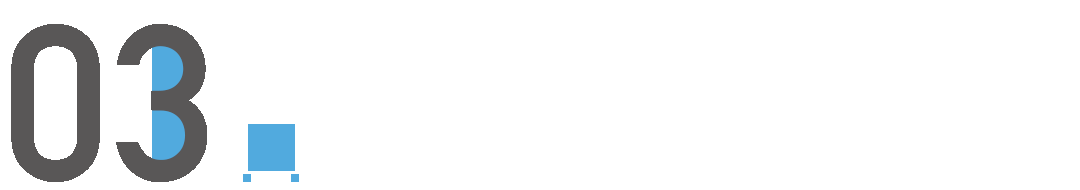
生与死攥回自己手中
在长达4年的志愿者生涯中,我虽然没有像个案老师一样,从头到尾地了解过患者的经历,但在每周两次的洗头、理发、芳香呵护服务中,也能接触到很多临终患者。
秦主任曾说,每位生命末期患者都是我们的老师,生命教育生命,生命影响生命。
我见过从容淡定的女患者,在病房的每一天都打扮精致,以最美的姿态迎接生命终结;也见过80多岁非常抗拒肌肤接触的老人,在芳香呵护的抚触下渐渐松弛,流下热泪;还有不到40岁的青年人,在妻儿精心准备的生日会上,与死亡和解。
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患者,曾是一名军人,他抵达病房时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身体不适,因为忍痛,很久没睡过一个安稳觉。在医生的建议下,我和三位经验丰富的志愿者决定为患者做一次芳香呵护,想让他试试看能否入睡。
过程中,患者很快睡着了,在精油的滋润下他的肌肤也从干涩变得柔软,可就在这时,我猛然觉知到手中似乎有东西,低头一看,竟是满手的泥球。我心里一慌,手上动作停滞了一秒,熟睡中的患者似乎感受到了我的情绪,手向后缩了一下。
虽然整个芳香呵护服务完成的很圆满,患者家属也对我表示感激,但那一刻的迟疑,还是让我深刻反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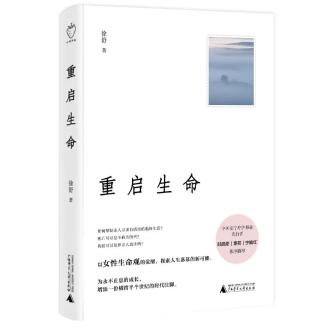
徐舒根据自身经历写的书《重启生命》
志愿者服务要带着无条件、无差别的爱心,可真正做起来却很难,我会被军人患者身上的泥球所干扰,这就是内心不接纳的表现。那一刻,我觉察到自己距离平和、淡然、无条件的接纳似乎还很远。
这些我亲眼所见的生死案例,让我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。
学习安宁理念后,我对死亡的恐惧逐渐消失,并开始学会接纳自己,用喜爱的事物滋养自己,让自己被爱充盈。
我喜欢摄影,那就背起行李跟摄影老师去沙漠、去森林,看风沙漫天,看绿林满地。
最近我又迷上了无人机航拍,跟着无人机老师踏遍新疆、内蒙,最近正在考虑去西藏。
我会刻意为安宁病房拍摄美丽的风光照片,也会征集我老师同学们适合安宁病房的作品,把最美的作品装裱之后挂在患者视线内的墙上。我希望患者在生命最后也能感受人间的美好,并带着这份美好印象离开这个世界。

安宁病房里,受捐的照片
如今,我的身后事也已经安排好。第二次乳腺癌复发时,我很淡然地做了断舍离,写下了遗书,也跟殡葬团队签了生命契约,安排我死后的遗体处理等事项。这样不给他人留下麻烦的提前计划,令我很心安,可以轻松无忧的放飞自己。
如果生命垂危,我会把自己交给安宁病房。
若那时还清醒,我会用最后30分钟给自己化个淡妆,穿上美丽的衣服,跟身边每位亲朋、志愿者拥抱道别。最后10分钟时,请任何人都不要来打搅我,我想亲自体验一下从此岸到彼岸的过程,因为我很好奇那是怎样的旅程。
死亡既然逃无可逃,那就与它和解,并臣服。

徐舒在新疆魔鬼城
前几日,我去医院复查,之前手术中漏切的一个结节发生了癌变,大小从直径1厘米增至1.6厘米,医生建议做个穿刺,判断是恶性还是良性。
可我觉得,良性也好,恶性也好,我都不想再去刺激它,就让我与它共存吧。
死亡随时可以来,我早已做好准备。
首图源于电视剧《重启人生》。文中配图均有受访者提供。
原标题:《照顾94岁父亲离世,我找到了最体面的死亡方式》